阅读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两种方式 | 彭莹莹X郭玉梅
发布时间:2022-10-13 来源: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浏览人数:3380人次北京时间10月6日,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殊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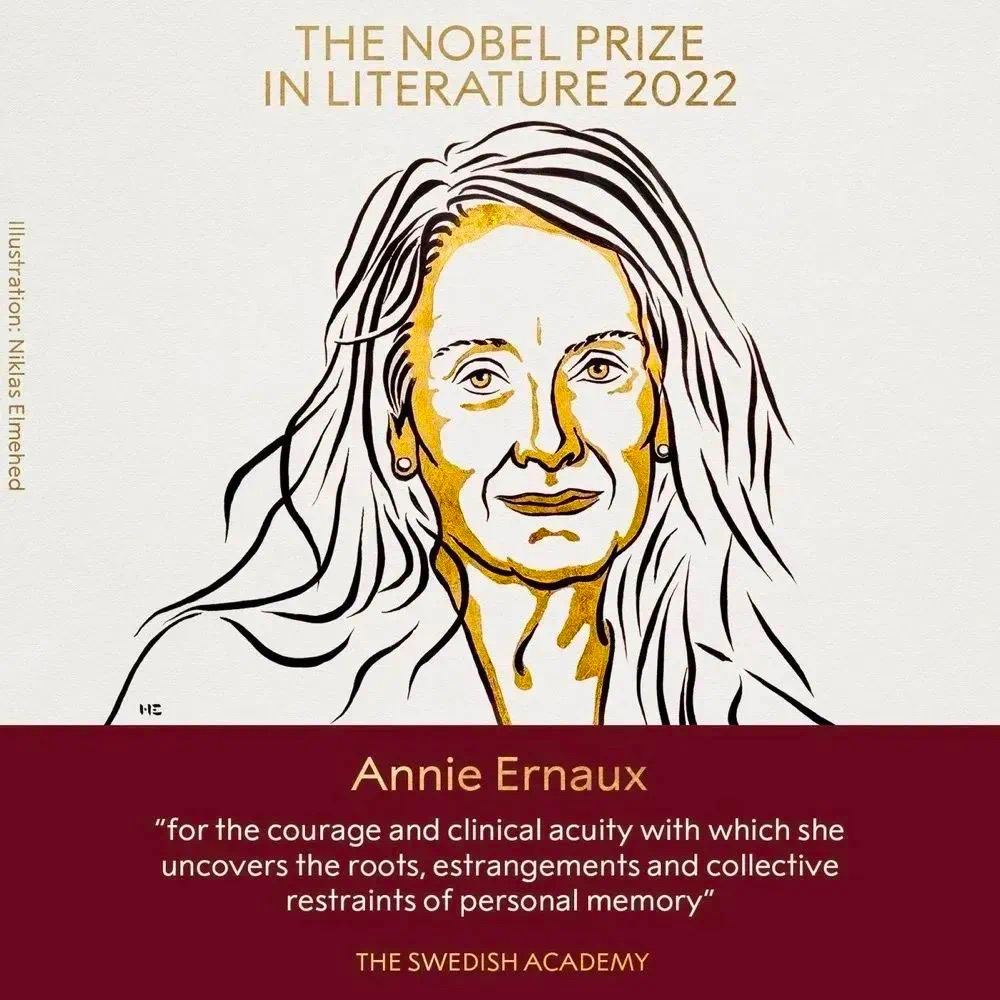
获奖语:以表彰她以勇气和敏锐揭开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束缚。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当代具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不过,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尽管她的部分作品已被译成中文,很多人对她的了解还是有限,甚至有网友在翻阅了几页《悠悠岁月》后感觉不明所以。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安妮·埃尔诺?她有哪些代表作?她作品的过人之处在哪里?对于她而言,人生与作品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在此,我们特刊发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彭莹莹与天津外国语学院法语系郭玉梅的文章,希望与你一起探索安妮·埃尔诺所营造的文学世界。
彭莹莹:第一人称的多义内涵,
使“个人传记”成为
“社会传记”
在传统的第一人称写作中,“我”作为单数形式的人称代词具有指代明确、统一的特点,勒热纳的自传契约更明确了“我”作为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同一指代。在安妮·埃尔诺的自传中,叙述者“我”在不同文本却具有不同的指代对象(主人公本人、社会群体中的某一个体甚或是某个社会群体),表现出虚构性、自传性、复数性和嬗变性,第一人称被赋予多义的内涵,成为埃尔诺所谓的无人称形式。“我”的多义性赋予个人叙事以普遍意义,从而使埃尔诺的“个人的”传记成为“社会的”传记。
埃尔诺的写作即始于第一人称。在第一部作品《空衣橱》里,“我”讲述了自己大学时期因意外怀孕不得不秘密堕胎的经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作者宣称的绝对真性,带有明显的自传特征。然而,随着对第一人称写作研究的深入和创新,学者们在发现了埃尔诺所采用的碎片式的写作方法、文本的高度口语化明显有别于传统自传。对于如何定义埃尔诺的作品的争论愈发激烈,出现了自传、自我虚构、新自传等提法。
尽管后来众多对埃尔诺文本的互文性研究表明《空衣橱》中那个叫邓迪丝的女孩讲述的正是后来《事件》中安妮的故事,但“自传不是猜谜游戏”,作者有意隐瞒了她与主人公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勒热那将此称为“自传体小说”。加斯帕里尼在总结的十条“自我虚构”的原则中第一条即规定了作者和主人公-叙述者的同 一性:“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有同样的名字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自我虚构)的第一个标志……自我虚构与自传体小说的区别即在于此,自传体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作者不具有相似的名字。”《空衣橱》中的“我”是作者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带有小说的虚构色彩,可称为“虚构的我”。
其后,埃尔诺连续出版了《位置》、《一个女人》、《走不出的黑夜》,以叙述者“我” 的视角讲述父亲和母亲的一生。“我”被放置在一个典型的小商人家庭环境中,目睹父母从小乡村走出进入工厂务工,最后苦心经营一间小小的咖啡-杂货店,实现了从农民—工人—小商人的社会阶层迁徙过程。“我”作为他们生存经历的见证者,在父母过世后以回忆的方式记录下这一段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在这些作品中,虽然讲述的是父母和家庭的故事,“我”是叙述者和见证者,并非主人公,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我”仍然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这些事件的当事人,他们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单纯的激情》、《占据》和《迷失》是埃尔诺创作主题转型的三部曲,讲述“我”所经历的两段失败的感情。在几次内心独白中,“我”称呼自己为“安妮”。埃尔诺在与让奈的访谈中也承认:“文本中的‘我’和封面上的署名指的是同一个人。”埃尔诺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承认了这份“身份同一性契约”。因此,这里的“我”可以被看作自传的“我”。
90 年代的《事件》和《耻辱》中实际上是以前故事的重复。重复的仅仅是故事,视角却大不相同。埃尔诺认为并不是要在写作中找到自我,而是“将‘我’放在更广阔的现实中”。此时,“我”既是传记的叙述者、故事的主人公,同时也是一段社会历史的见证者、记录员,更是群体中的代表之一。第一人称“我”因此具有了复数意义。
《外部日记》和《外面的生活》中,埃尔诺将目光投向了身边形形色色的小人物。 “我”观察着、记录着地铁里卖唱的年轻人,街角乞讨的流浪汉、超市的收银员。“我”像一个隐形人,只作为叙述者存在,而不出现在文字中,哪怕只有一次出现,“我在火车站买了一份《嘉人》杂志看星座运程”,也要解释“第三人称他或她,是另一个人,可以想如何变如何。而‘我’,是我自己,不可能去看星座”。因此,叙述者“我”成了看不见的摄像机,正如《外部日记》 前言中解释的:“我尽量避免出现在镜头中……用一种摄影的写法记录真实。”“我” 弱化为记录第三者的客观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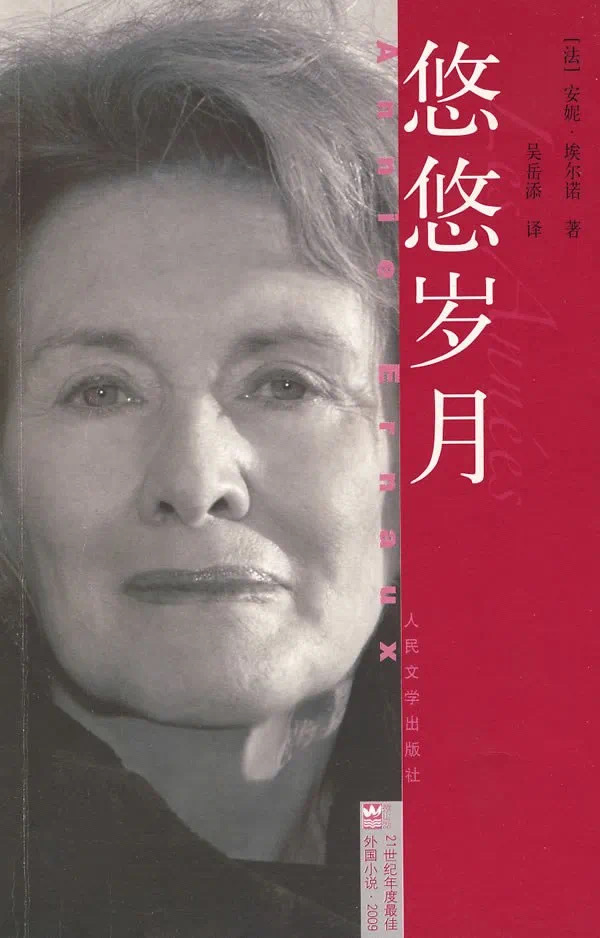
而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干脆放弃了“我”而用“我们”(on 或者 nous)来充当叙述者的角色,直接将“我”溶于群体价值中。她用一幅幅自己的老照片串起整部作品,“我们慢慢长大……我们开始走进校门……我们玩着手绢唱着‘你好纪约姆,你吃饭了吗’……”。人称形式的变化反映了叙述声音的变化,埃尔诺解释说“家庭故事和社会故事是一个整体”,在这三部作品中,文本中碎片式的背景描写弱化了个人故事的完整性,集中记录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意在“用影像的方式捕捉日常的、城市中的、集体的现实”。第一人称已经完全失去了个人叙事的内省意义,无论是哪种人称代词——“我”或是“我们”,都成为了叙事结构中的一个符码,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某个个体或是群体的代表,成为一种具有可变意义的代词来记录社会的影像。
显然,埃尔诺笔下的第一人称“我”已超出了自传契约对身份同一性的界定范畴。在其不同作品中,“我”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指代对象。从个体的人生经历中虚构出的“我”带有自我虚构的色彩;自传的“我”回忆个体的心路历程,记录一段家庭的历史;复数的 “我”还原出一个社会人的发展轨迹;最终,嬗变的“我”直接用复数人称掩盖“我”,直接将“我”的记忆融于一段社会历史。“我”,不再是单一内涵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而被赋予多意的内涵,成为埃尔诺所说的“我”的无人称形式。
可见对于第一人称“我”的使用,埃尔诺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我”的内涵和指代反映了埃尔诺的“个人的”到“社会的”传记的变化,从对“我”的人生故事到对普遍意义的社会人生的思考。埃尔诺的文学之路始于个人的回忆,却并未局限在传统自传的狭义定义中。她经常把目光聚集在周围的人和事,将自我至于周遭的人事之中,又在周遭的人事之中重新发现自我。一切故事缘起“我”的回忆,又处处折射出“我”对社会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正如萨维昂所总结的:埃尔诺的作品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奉行的一整套价值观和态度,成为个人的和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和主人公,完成了一部恢宏的“社会自传”。
郭玉梅:写实与心理相融,
既是回归传统也是现代主义的升华
埃尔诺是当代法国文坛上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和简洁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战后法国的平民生活,尤其是那个时代的法国女性的内心世界。
1974年,安妮·埃尔诺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空橱柜》问世,至今已发表有十余部小说。她的小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位置》、《一个女人》和《耻辱》为代表的自传体小说,另一类是以《单纯的激情》和《迷失》等为代表的“私人日记”式小说。这些小说的发表每每引起轰动。自传体小说《位置》和《一个女人》分别创造了五十万和四十五万册的销量,引起了法国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其中,《位置》荣获了1984年雷诺多文学奖,并由此进人了大学的课堂,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
她的作品题材朴素,视角独特,笔调平实,体现了一种追求写实主义与心理描写相融合的风格,这在历经现代主义众多流派洗礼的法国世纪文学中,既代表了某种回归传统,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某种升华。对此,虽然批评界尚有争议,褒贬不一,但这种独特风格至少已使她在法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现在通过对安妮 · 埃尔诺的《位置》、《一个女人》和《耻辱》三部小说进行剖析来探讨她所特有的女性文学创作特色。
安妮 · 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青年时代就读于鲁昂文学院和波尔多大学,获得现代文学教师学衔。她幼年家境拮据,父亲阿尔封斯杜塞斯原是一家农场的雇工,后又在工厂当工人,婚后与她的母亲布朗什·杜梅尼在一处贫穷的街区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兼杂货店,过着平民的生活。
小说《位置》、《一个女人》和《耻辱》等,表现了这个时期平民阶层的生存图景。《位置》、《一个女人》和《耻辱》均属自传体小说,均使用第一人称叙述, 既是叙述者又是女主人公,作品的“女性特征”可谓直截了当。这三部小说分别讲述了出身贫寒的“我”与父亲、母亲之间既亲近又隔膜的复杂情感。
她在《位置》中是这样说的“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写他的生活,写我少年时期与他的隔膜,而这种隔膜其实是一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传的,就像不得不分手而又情思不断的那种东西。”
小说以真实平实的笔触,仿佛是记录了“我” 在父母的期望与呵护下朝布尔乔亚阶层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内心世界和外在环境之间的不平衡,通过叙述“我”与父母亲渐渐产生隔膜的过程,写实性地再现了法国战后时期下层百姓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
安妮埃尔诺自己写道 “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什么东西吧。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人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环境里不觉得太孤独和虚假。”(《一个女人》)。

“我明白写小说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要叙述一个为生存而奋斗一生的人,我没有权力将我写的作品称为艺术,更不能追求作品如何如何令人激动。我只是要把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事客观地记录下来。”(《位置》)从作者的上述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追求的就是要用一种平实的语言记下社会历史真实的一幕。
这种写实风格一直是安妮埃尔诺小说创作的指南。
由于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和女主人公合二而一,她在用她的视角解读、体验和描述世界,她的作品读起来似乎永远都是些和她血肉相连的真实故事。其实我们不必去严格考证每个细节的真实性,我们更在意的是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写实的风格。
她拒绝某些同时代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法国人的生活图景,在她看来,那些故事对多数法国人来说是不真实的,更像是人们刻意杜撰出来的“我读普鲁斯特或莫里亚克的作品时,我觉得他们讲述的并不是我父亲童年时代的那种生活,而他们讲述的那种生活方式还属于中世纪。”(《位置》)。她说“我的信条只是诚实和准确。”
我们承认安妮的女性自传体小说创作书写的大多是个体的感受,讲述的是女性人物自己的故事,但她的叙述也涵盖了一般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和群体。 在她的作品里,个人和社会的维度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运用个人的故事去理解和展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这种手法拓展了传统女性文学狭隘的视野。特别是作者把握了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内涵,体现了一种具有现实主义深度的女性文学的美学价值。换言之,她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个别女人生活的实录,而是成为了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由此可见,她的这种写实风格体现了法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在回归传统的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她在心理描写方面也吸收了某些现代主义的元素。
安妮 · 埃尔诺作品的主题大多建立在女主人公的私人生活之上,涉及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和她自己的爱情,属于“私人叙事” 一 类,其中表现最多的莫过于展现女主人公的情绪、体验和心路历程。因此,安妮 · 埃尔诺的这种女性视角下的心理描写就成了她的作品的一大特色。
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出身卑微,但天资聪颖。她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在私立学校里学习优秀。但她的思想也由简单而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在与同学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有同学要来她家里玩,她总是要事先对同学声明“你知道吗,我们家很简陋”即便是“我”结婚后,在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丈夫家里 ,这种潜藏她在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依然挥之不去。对于已经进人了另一个阶层的“我”来说,与父母的那份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生她养她的父母,是希望她“生活得比自己更好”的亲人,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亲人之间不再有的心心相印的理解,在心灵上的无法沟通,因此,“我”无可避免地陷人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痛苦之中,那是一种深隐于内心的痛苦,是一种心灵的煎熬,“我” 把这叫做“内心的流亡”。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来源于她同时生活于两个阶层。她在平民阶层里长大,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同时她又跳出了原在阶层的梗桔,升人了一个更高的阶层,然后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俯瞰她所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而作者要解析清楚这“内心的流亡”,则完全有赖于细腻的心理描写。我们不难发现,在女主人公讲述的故事中,写实式的叙述与心理描写已经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例如《位置》和《一个女人》在追忆父亲、母亲一生的多个瞬间时,叙述者兼女主人公常常把叙述往事的进程暂停下来,把读者从往事所处的“过去” 拉回到她“写作时的现在”,详细讲述她在写作每个片段时的感受,发表一番议论。作者通过这种夹叙夹议的叙事方法,把过去的场景与“现在”的情感交织成一个特殊的时间图景,使追忆者女主人公通过“现在”这个平台去透视“过去”,使“过去”变得更加清晰,使意义与情感更加厚重。其实我们尽可相信作品中的“我”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又不一定完全是她本人,因为我们这里要做的并不是发生学考证,而是对文本风格的美学批评与欣赏。
这里有必要提及小说《耻辱》采用的倒叙的方式。故事以父母的一次吵架为开篇。父亲在盛怒之下声称要杀掉母亲,这件事给“我”的心灵留下了“耻辱” 的创伤。文本开篇即扣题。之后,作者选取的材料全部围绕着“我”感受到的“ 耻辱” 这一心理主题进行。作者通过聚焦拍摄于不同时期的“我”的老照片引发 回忆像放映幻灯片一样把不同时期的“我”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把一个个过去的生活碎片按照事件的逻辑和记忆的头绪进行艺术重组。在这里,个人的主观情感与心理变化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支配着文本的延伸,让回忆与现实在叙述中交叉、跳跃。如果说“耻辱”是小说的心理主线的话,那么父母吵架这一场景就是小说的中心事件,小说由此从“我”的童年向成年延展。通过成长中的女性的独特视角凸显了法国当时下层百姓的生活艰辛与“我”在私立学校接受的上层社会的“正统”教育之间的矛盾,小说在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中寻找着个人与时代及社会的某种联结,这无疑让人想到了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 中对爱玛命运的安排。从叙述方式上讲这种以人物心理活动主导叙事的手法 ,也很有些意识流小说和新小说的味道,读来很是令人遐想和回味。
安妮 · 埃尔诺的作品大都短小精悍。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波澜起伏的复杂故事情节,看不到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描写,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对日常琐事的回忆。安妮 · 埃尔诺的小说大多采用平淡的叙事语气。她尽量将自己的情感压抑在平淡的如同潺潺流水般的述说之下,让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地展露 ,让生活的本色呈现出来。
例如“对于我的父亲,讲方言土语就代表着过时和丑陋,就意味着低人一等。父亲在咖啡馆里和熟人在一起时很喜欢聊天,可在那些法语讲得很标准 的人面前,他就会不哼不哈,保持缄默,或是话说到一半停下来,伴着手势说 ‘是不是’或者干脆就只用手势示意对方,让对方接着替他说下去。父亲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唯恐说错一句话,会像当众放屁一样出丑。”(《位置》)
在语言的运用上,安妮·埃尔诺用词之清淡是绝无仅有的。她的作品语言自然,简洁流畅,朴实无华,然而实际上却是独具匠心的。她从不使用冗长而复杂的句子,多采用单部句、省文句、以及结构松散的日常口语句式,通俗易懂。她很少使用具有夸张色彩的形容词或修饰语,并认为只有白描的写作手法才是最精确的。
她说 “女性小说中近乎疯狂地使用那么多的形容词,如傲慢的神态,阴郁的声调,傲慢的语调,冷嘲热讽的口吻,尖刻的语气等,我想不出现实生活中周围的人有哪一个可以用这样的词来修饰。我觉得我一直是在使用着这种当时很物质化的语言来写作,而不是用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词汇来写作。 我永远也不会领略运用比喻方法的神奇以及运用文体修辞的喜悦了。”“我尽量地使用一些众所周知的词和句子,……而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这些词,这些句子能表现一个限度,一个内涵,勾画了我父亲的形象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色彩,这一点是绝不会张冠李戴的。”(《位置》)
当然,平淡不等于乏味。这需要作者极高的功力。这种写作风格,加强了作品厚重的现实感与真实感,透出了作者追求真实叙事的努力。简洁清淡的语言已成为安妮·埃尔诺表达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也构成了她的小说的一大美学特色。
通过阅读这三部小说,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安妮·埃尔诺:她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窥探着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批评界有些人认为她过于沉湎于普通人的生活。可安妮则认为,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诠释真实才是艺术的最高命题。谈到小说的形式,她认为,是有事要说才导致说话的形式。她从新小说那里得到的启发就是“写作是探索一种形式,而不是复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她没有犹疑和惶惑,她称自己并没有对什么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的真实抒发。这也许是对其创作风格的最好注释。
地址:武汉市解放公园路44号
电话:027-82605800/82624796
传真:027-82624796



